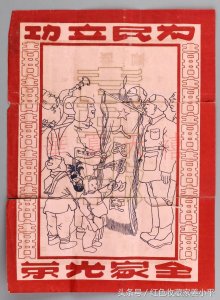《天黑得很慢》:文学对衰老的回答
【财新网】(实习记者 佟宇轩)“人步入老年就像天渐入黑夜,因为天黑得很慢,你还可以做一些事情。也因为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,所以可能出现各种问题,你要准备去承受。”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近日推出了长篇小说《天黑得很慢》,聚焦老龄社会中种种现实问题。
2018年4月5日,周大新在北京角楼图书馆举办新书分享会,讲述创作背后的心路历程。
天黑前要经历的几件事
用周大新的说法,《天黑得很慢》采取的写作手法是“拟纪实”。本书以“万寿公园” 中的七个黄昏为线索,讲述护理员钟笑漾陪伴退休法官萧成衫度过晚年的故事,展现了“黄昏恋”“失独老人”“不实宣传的医疗保健品诈骗”“阿兹海默症”等等老年人群可能面临的种种问题。
书中,萧成衫“黄昏恋”未果,又痛失独生女儿薇薇,与护理员钟笑漾相依为命。而钟笑漾被男友抛弃,成为单身母亲,想要与男友同归于尽时,被被萧成衫及时发现并制止。她为了使儿子落户北京而与萧成衫注册结婚,共度天黑前的最后人生。
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。根据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消息,截至2017年底,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.41亿人,占总人口17.3%。而一般认为,60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达10%,即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。
而据人口学专家、《大国空巢》作者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:中国现有的2.18亿独生子女,会有1009万人在25岁左右之前离世的人。这意味着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。
缺乏专业陪护、慢性疾病缠身、与子女异地相处或阴阳两隔、身心孤独无爱可诉……种种现实困境在老龄社会浮出水面,成为当下亟待面对的问题。小说前四章引入一些对科技的想象,借用陪护机器人、“长寿药丸”、“返老还青虚拟世界技术体验”等概念,试图给出应对老龄社会、提高老年生活质量的方法。方法各异,希望有之,荒诞有之。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说:“如果永生的前提不是像现在这么老,而是重新填满皮下脂肪,器官也像年轻人那样,要是这样,我愿意长生不老。”
尽管悉数了老龄社会的困境,小说依然以爱与陪伴为主线,给出温暖的结局。周大新说:“年老之后,人们会逐渐明白,人到世上就是获得爱、给予爱的过程。小时候是获得家庭、社会、学校的爱,毕业后开始为社会、家庭付出。爱与被爱是活着的目的与动力。你要相信,爱是温暖老人和整个社会的东西。”
原来衰老可以如此具体
周大新1952年出生在河南农村,1985年毕业于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,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处创作室专业作家。他的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《走出盆地》《第二十幕》《21大厦》等,中短篇小说集《汉家女》《香魂女》《银饰》《左朱雀右白虎》等,其中三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,六部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。
出版于2006的长篇小说《湖光山色》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故事发生在丹江口水库,描述了一个曾在北京打工的乡村女性暖暖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经历,通过日常叙事将中国乡村艰难发展的思考娓娓道来。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曾评价说:“在河南作家擅长诡异怪诞的路数中,周大新的风格显得平实婉约,他细腻舒畅反倒显得别具一格。这部小说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,也包含着怀乡的感情,所以小说写得流畅舒缓,虽有矛盾,但没有痛不欲生的悲怆。整部小说还是如湖光山色,清新可人,给人以阅读的快感。”
新作《天黑得很慢》是周大新对自己人生的反思。“年轻的时候,我总觉得衰老离自己太远,也不愿意去想。也许,把不敢面对的事情往后搁置,是人的一种本能。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,我不得不去想。”
触动他写下这本书的有几件小事。一日,周大新在楼道中遇到一位老太太,手里拿着两个洋葱,看着楼层发怵:“两个洋葱太沉了,我不知道能不能拿上去。”周大新帮老人拿上楼,但不理解“两个洋葱算什么重量”,直到日后回想,突然意识到,原来人衰老以后,体力下降如此之大。两个洋葱对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年人来说,已经是很重的负担。那是他第一次被衰老触动,发现衰老是如此具体。
还有一则新闻让他印象深刻:广州一位老作家和妻子同居一个卧室,分床而住。半夜,妻子还听见他打呼噜声,但早上起来却发现老作家已经因为心肌梗塞去世了。“两人仅仅是一米的距离啊,在疾病下都无法发出呼救,真是很可怕。”晚年独居的张爱玲在公寓中去世,三天后才被邻居发现。诸如此类的事情,让周大新有了书写“衰老”的想法。
这本书也是他对自己困扰的一种回答。“在写这本书之前,我是很害怕衰老的。但写完这本书,我也渐渐明白,每个人都会经历变老,是人类的普遍体验。既然是规律,就要勇敢面对,写完之后内心平静了一些。衰老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你把人生前面很好的一些段落都过去了,现在就必须要面对衰老。”
周大新家附近有个玲珑公园,这也是书中“万寿公园”的原型。他常常在公园中散步、看书、写书法,还在家中专门装修了一个家庭影院,每晚看一部喜欢的电影。他甚至规划了“万一以后动不了了”的生活——在床对面放一个大电视机,晚上还可以看电影。他说,“这是我理想中的老年生活,和年轻时候状态差不多。设想得很美好,但还是要看造物主的安排。”
文艺作品中的老年
衰老是中西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题,作家对此话题的思考呈现多样性。许多文学作品中,“衰老”是颇具悲情色彩的词汇。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邓中天曾在《面对衰老,文学何为——文学老年学与衰老创痛》中总结,“海明威等一大批作家直接将老年等同于死亡,而在奥斯特等一批后现代作家看来,老年形象被用来思考整个人类文明的衰老与死亡。也有作家比如菲力普·罗斯、多丽丝·莱辛等,用老年便溺失禁来隐喻死亡,突显了衰老与死亡的关联深深地扎根于人类文化传统之中,看到了衰老对生命质量的威胁,也看到了灵魂无所归处的苦闷。”
而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则在《优雅地老去》中将历经漫长人生和岁月磨砺、心灵深处潜藏着光芒的人们称为“白金一代”,并提出这一代的誓言——我们,不被世俗左右,充满好奇心态,追求人生所爱;不惜赞美他人,不忘自赏自爱,优雅洒脱有点“坏”!他倡导老人们做个“与年龄不符”的人,这无疑是对传统老年观念的一种反叛。
新中国的文学作品对老年人的书写也呈现出了多元的语调。“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安”描绘了中国人理想的老年生活图景。学者张文斌在《新世纪文学老年叙事研究中》指出:“无处逃遁的衰老病死、无处诉说的孤寂苦闷”,是新世纪文学深切关注的图景,而类似于《英雄》《找乐》等展现“人生七十好年华”主题的作品相对较少,文学作品中“老骥伏枥、志在千里”的老年形象并不常见。相比于对“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、老有所安”的关注,“老有所乐”仍然表现不足,老年人依然是“安享晚年”而非“创造新天地”的形象。
如今的中国有越来越多讲述老年群体的故事。文学作品《疯祭》《空巢》《一百零八》《父亲不哭》,电影《桃姐》《飞越老人院》,电视剧《老爸的爱情》《谁来伺候妈》《老米家的婚事》等,均体现了对老年群体的关怀。
但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作品,老年叙事仍然占比较小。正如周大新所言,“进入老年,关注你的人越来越少”,主流文学对于老年生活的书写仍然是有限的,需要进一步被关注。■